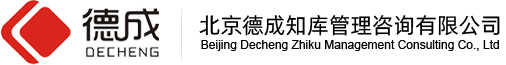慶歷三年九月,以天章閣對策范仲淹呈獻仁宗《答手詔條陳十事》為標志�,一場以仁宗為主導(dǎo)�,以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為操盤手的慶歷新政拉開序幕了�����。仁宗發(fā)布了一系列改革詔令����,序次推進范仲淹的十大新政措施��。地方官吏的品德賢愚與否關(guān)乎一方百姓的休戚,范仲淹要求把那些身體不好�、品德不好、能力不好的不合格官員一律罷免����。慶歷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張溫之為河北都轉(zhuǎn)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zhuǎn)運按察使�����、沈邀為京東轉(zhuǎn)運按察使��、施昌言為河?xùn)|都轉(zhuǎn)運按察使,按察本路州縣長吏�����,專門奉命搜集各州縣地方官的過失���,相當(dāng)于今天的中央派出巡視組對地方進行專項巡視����。這樣,十條中的第四條(擇長官)首先見之于行動�����。范仲淹個性耿直����,見不得庸官靠走后門上位�,眼睛里容不得沙���。景佑三年(1036)年�,他就把京官晉升情況繪制成一份《百官圖》����,譏諷宰相呂夷簡不能選賢���。范仲淹意氣風(fēng)發(fā),把各路巡視組匯總上來的名單,親自審查����,見有不合格者����,抑或也有不順眼者,就大筆一揮毫不留情地圈去�����,被圈掉的名單一大排。富弼覺得有點過��,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于是就提醒他“你大筆一勾容易�����,可你知不知道那被勾去的筆后是一家子人的哭?”范仲淹理直氣壯地回了一句堪稱經(jīng)典的話:一家哭總比不上一路哭吧!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詔����,施行磨勘新法,明黜陟也就見之于行動�。新法規(guī)定:除有特殊功德和政績的,不得破格升遷任命官員,有問題被罷免的�,不許轉(zhuǎn)官帶職����。京官任職三年,無犯罪記錄且有五位清望官員保薦的�����,才可獲準晉升���,否則就要延遲等待。候選的官員要參加考試���,并有京官三人保舉才可以補官��。沒有才干�、貪莊枉法、年老體衰、膽小怕事的官員須革除不用���。十一月十九日�����,朝廷按照“蔭親”����、“蔭貴”的原則對恩蔭制度作出新規(guī)定�����,以抑制“旁及疏從”���,蔭補過泛����。如,皇帝生日不再蔭補��;官員長子以外的子孫需年滿十五����,弟侄需年滿二十,才有蔭補資格��;官階較低官員只能蔭子或?qū)O一人����,減少了名額�����;蔭補子弟必須通過禮部考試才能入仕為官����,其補授官階的高低視受恩賞官員的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定�,等等。慶歷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朝廷頒布貢舉新法����,下詔興學(xué)���,以“精貢舉”為主要內(nèi)容的教育改革全面推開���。范仲淹��、宋祁、歐陽修等八人向皇上合奏:“教不本于學(xué)校,士不察于鄉(xiāng)里�,則不能核名實;科舉束于聲病����,學(xué)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也就是說�����,教育游離于學(xué)校之外,士子考察不問鄉(xiāng)里的情況����,科舉考試只注重詞賦、記誦���,考不出品德,考不出才能���。他們的奏議是一項旨在把科舉與學(xué)校教育結(jié)合起來以選拔培養(yǎng)合格人才的教育改革的宣言書����。慶歷興學(xué)包括如下舉措。第一���,號召州縣立學(xué)����。選好宿學(xué)之士來充任老師;規(guī)定學(xué)時����,參加應(yīng)舉士子必須在學(xué)校習(xí)業(yè)300日以上���,是全日制的����,不是走讀的,如此才允許參加考試����;參加州縣考試的士子要考察品德����,并有人為此予以擔(dān)保�。第二���,振興太學(xué)。在“教”的環(huán)節(jié)上堅持德才標準�,選用擁護新政的名師學(xué)者石介�、孫復(fù)等主持太學(xué)講席;在“學(xué)”的環(huán)節(jié)上擴招生源,允許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學(xué),生源名額從七十名增至四百名����,進入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期����。第三���,改革科舉考試�。調(diào)整考試內(nèi)容,突出時事政務(wù)��,強化策論����,弱化詩賦�,取消貼經(jīng)墨義(貼經(jīng)即以紙貼蓋經(jīng)文,讓考生背誦����;墨義即背誦經(jīng)文的注疏)�。慶歷興學(xué)激發(fā)了地方辦學(xué)的熱潮。據(jù)歐陽修《吉州學(xué)記》記載:慶歷興學(xué)詔下之日,"吏民感悅����,奔走���,執(zhí)事者以后為羞����。"可見�����,官府和百姓都拍手稱快��,以興學(xué)為榮�,落后為恥����。官府出資給力��,社會賢達捐資贊助�����,百姓出工出力,多方合力共建����,各地爭先恐后,辦學(xué)熱情空前高漲�����。范仲淹等人力圖將學(xué)校教學(xué)、科舉取士和經(jīng)世致用三者統(tǒng)一起來����,形成一個以學(xué)校為載體、科舉為手段�����、社會需求為歸依的教育體制����,這是自科舉制度創(chuàng)設(shè)以來,第一次針對學(xué)校教育片面附庸于科舉而不注重社會功能的狀況所進行的改革嘗試����,其目標雖因后來改革的中斷而未能達到�,但對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慶歷三年十一月,朝廷下詔“限職田”(“均公田”)�����。地方官的職田制的定額數(shù)量�����、等級標準等還是在真宗朝時制定的����,歷經(jīng)40多年的運行,產(chǎn)生了多寡不均��、苦樂懸殊的情況��,挫傷了地方下層官員的積極性��。這次改革主要是適度降低各級地方官的職田標準,緩解多寡不均的矛盾�����;對標準線以下不足的部分要限時補足數(shù)額���,政策向基層傾斜,確保地方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待遇有保障�,樂于在地方���、在基層干事創(chuàng)業(yè)。對此�����,朝廷還派員檢查督辦��,力促地方州郡抓好落實�,調(diào)動地方官員的積極性。經(jīng)濟方面的改革共有兩條����。其一����,興修水利以“厚農(nóng)桑”����。具體做法是在每年秋收以后,朝廷行文諸路轉(zhuǎn)運使,督導(dǎo)州縣結(jié)合自身特點開展農(nóng)田水利基本建設(shè),修河、開渠����、筑堤等�,夯實農(nóng)業(yè)基礎(chǔ)���。其二、省并縣邑以“減徭役”�。精簡機構(gòu),調(diào)整區(qū)劃,把那些管轄地域小、人口不多的縣進行撤并����,減輕政府行政成本和百姓負擔(dān)�。慶歷四年五月��,撤銷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的五個縣��,降格為鎮(zhèn)而并于鄰縣����,每減少一縣可以減少役戶二百余戶��。關(guān)于“覃恩信�、重命令”不過是強調(diào)詔敕政令信用,注重落實���,言必信,行必果��,法必依���,違必究�,談不上制度層面的改革。加強軍備的措施僅一條���。范仲淹建議恢復(fù)唐代府兵制,但這條措施未及實際施行����。自古以來����,給人奶酪的事好辦�����,動人奶酪的事不好辦�����。慶歷新政動的可不是一般人的奶酪���,而是動了當(dāng)權(quán)者的奶酪,事情當(dāng)然更難辦了�。因此��,動奶酪者與護奶酪者之間的斗爭就如影隨形����,暗流洶涌���,不可調(diào)和�?�?傮w而言����,在斗爭策略上��,力主動奶酪的改革派赤膊上陣����,行事剛烈�,方法簡單���,缺乏權(quán)謀;而全力護奶酪的保守派則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們不正面跟你談動奶酪的“事”�����,而是聲東擊西、圍魏救趙地談“人”�����,從人事下手,步步為營地對新政組織者與支持者進行打擊�����,消滅你的有生力量�,直至把你打倒�����。于是�,一方面是新政詔書頻發(fā),另一方面圍繞范仲淹等改革派成員的人事斗爭紛繁上演�,構(gòu)成了慶歷新政的一道獨特的風(fēng)景����。與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同時上演的還有一出大戲���,那就是震動朝野的滕宗諒事件。滕宗諒何許人也�����,凡上過中學(xué)的人都記得范仲淹在《岳陽樓記》的開篇中說到:“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文中的那個滕子京就是滕宗諒����。他與范仲淹同年考中進士����,在當(dāng)時,稱為“同年”��。滕宗諒作風(fēng)潑辣��,做事果斷,還又勤政廉潔����,在地方上政績也不錯�,就是不注意小節(jié)��。在范仲淹的舉薦下�����,滕宗諒調(diào)任到西北前線任地方官“知慶州”�,其時范仲淹正是西北前線軍事負責(zé)人���。他們一起在西北共事4年多�����,彼此惺惺相惜,知根知底����,心中都只有大宋江山。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發(fā)滕宗諒先前在涇州任職時�����,嚴重侵吞�、挪用公款,請求朝廷調(diào)查。監(jiān)察御史梁堅堅持即刻罷免滕宗諒�����,并將其下獄審查�����。仁宗覺得負責(zé)紀檢的人員有些小題大做����,但還是派人調(diào)查此事����。一宗普通的而且有點“子虛烏有”的貪腐案����,把當(dāng)時朝廷御史臺(王拱辰�、梁堅)��、兩府(范仲淹、富弼)�、諫院(歐陽修)三股力量都絞進來了,范仲淹等在仁宗面前為滕宗諒傾力辯護��,而王拱辰���、梁堅等則是誓死要嚴查深挖�����,雙方斗爭十分激烈��。處于斗爭漩渦中的滕宗諒此時很不冷靜,一方面他覺得自己在前線為朝廷賣命�����,對大宋忠心耿耿�����,還受此冤屈,心中憤懣���;另一方面他又怕連累正在朝中主持改革大業(yè)的范仲淹等好友��,一氣之下把相關(guān)記錄文件及賬本給燒毀了����,這下就把本來沒什么原則問題的案情燒成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賬了。負責(zé)監(jiān)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更是抓住不放,以辭職相要挾���,而且真的不來上班了���。最終,仁宗在這場府臺之爭中倒向了反對派,于慶歷四年正月���,將滕宗諒降職處罰�,先是知虢州,隨后又改知偏遠的岳州(不過����,這一改成就了千古美文《岳陽樓記》���,當(dāng)然這是閑話)��,滕宗諒案算是落幕了���。改革剛剛進行三個來月范仲淹就被無端地吃了一悶棍���,中傷不淺�����。你范仲淹不是要整頓吏治,大刀闊斧搞什么人事制度改革嗎����,怎么對別人就是鞭子嚴抽�����,也不管什么“一家哭”���、“兩家哭”的�����,而對自己人就搞“雙重標準”、“黨同伐異”�����,你還有什么資格來領(lǐng)導(dǎo)改革。反對派雖然沒有明說,但這頂無形的帽子算是扣實了�����。斗爭還只是剛剛拉開序幕�����,改革不停,折騰不息�����。新政實施后���,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變著法子把臟水往范仲淹等改革派身上潑�,毀謗新政的言論此起彼伏�����,“朋黨”的帽子滿天飛。慶歷四年(1044年)四月����,廣西宣州地區(qū)發(fā)生少數(shù)民族叛亂�����,這事本來跟改革派八竿子打不著的�����,可事情硬是被謠言扯上去了��。問題就出在庸碌無為的知州馮伸己��,他是前朝宰相馮拯之子,是太子黨�����,官二代�����。朝中流言莫名四起,說此前按察使已經(jīng)到該地檢查���,罷黜了一些不該罷黜的官員��,對庸碌無為的知州卻不敢動�����,由此延伸至范仲淹也是一個欺軟怕硬的假改革者。同月����,前任樞密使夏竦向仁宗奏報,說朝中有了第二個權(quán)力中心,即以樞密使杜衍����、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副使富弼����、諫官歐陽修為首的朋黨�。他們掌握著軍政及監(jiān)督調(diào)查權(quán),如此一來���,范仲淹一黨可以隨意捏造理由罷黜官員�,任命自己的人馬,一旦有變還可以調(diào)動軍隊�,天下危也���。這一下挫到了仁宗的痛處�����,祖宗家法的精髓就是“事為之防�����,曲為之制”��,防范一切可能,他對朋黨之論開始半信半疑了����。晏殊稟奏,中書省中已經(jīng)積壓了數(shù)百份彈頦范仲淹結(jié)黨的奏折��,御史中丞王拱辰處也接到不少官員的舉報�����。輿論對改革派很不利,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提出朋黨分“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理論來予以反擊���。尤其是歐陽修情緒激動����,把一身的才華抖露出來����,激情澎湃揮毫寫就了千古奇文《朋黨論》���,為改革清理雜音,提供理論支持��。文學(xué)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爭中有時會是敗筆�。這篇《朋黨論》幫了改革者的倒忙�����,如果說先前仁宗皇帝還是在內(nèi)心懷疑,那么這篇文章在朝臣中所引起的爭議則證實了他的判斷,改革派結(jié)黨是實�,勢力不小��。這觸犯了人主的忌諱�����,改革在悄然轉(zhuǎn)向���。在改革斗爭激烈的關(guān)鍵時刻,仁宗下詔委派歐陽修為欽差大臣����,前往河?xùn)|地區(qū)����,協(xié)同河?xùn)|轉(zhuǎn)運使,解決西線戰(zhàn)區(qū)糧餉供應(yīng)困難的問題�。這個時候把改革急先鋒調(diào)離出京�����,意味深長�。被貶外地的夏竦早就聞到了京城異樣的政治氣味。此人精于權(quán)術(shù)�����,才高德薄����,出于對改革派當(dāng)年扳倒他的怨恨�,他用陰險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改變新政方向與進程的“莫須有”栽贓事件�。他有一小妾,書法超群�,臨摹別人足以亂真����。在改革的關(guān)鍵時期,書生意氣的石介曾寫信給富弼��,勉勵他們堅持改革�����,“行伊周之事”。這年六月���,夏竦指使小妾仿照石介的筆跡�,把“伊周”改成“伊霍”��?���!耙林堋笔巧瞎艜r期的兩位賢臣良相,即商朝的伊尹和西周的周公旦;“伊霍”指的是伊尹與西漢的霍光���,二人都高居相位、也都干過廢立天子之事�,故合稱為“伊霍”���。這一字之改����,“行伊周之事”便成了“行伊霍之事”���,意思全變�����,把學(xué)習(xí)先賢��、激勵改革的“陽謀”,變成了私結(jié)朋黨�、鼓搗廢帝��、另立新君的“陰謀”��。為進一步坐實罪名�����,他還特地讓小妾偽造了石介為富弼起草的廢立詔書,然后散布消息���,把謠言傳到仁宗耳朵里?!暗垭m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時邊事再起�,年過56的范仲淹也不再像年輕時意氣用事��,滄桑老成的他感覺到了仁宗對改革派的失信,主動請求出京處置西線軍務(wù)�,仁宗批準了他的請求,任命為陜西��、河?xùn)|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八月,富弼亦以樞密副使離京����,出為河北宣撫使��。至此����,改革主將們已紛紛離京����,只剩相對中庸的韓琦還在京城。九月��,仁宗有意把陳執(zhí)中從外地召入朝中擔(dān)任參知政事����,新政派的諫官蔡襄和孫甫上奏說他處事武斷���,不學(xué)無術(shù)����,不是當(dāng)宰相的料����。仁宗根本不聽����,執(zhí)意調(diào)任,這是一個政治信號�。于是�,蔡襄和孫甫便知趣地自求外放��,仁宗二話沒說就同意了。至此���,臺諫官清一色都是反對派,改革失去了政治喉舌�。這一年可謂是改革的多事之秋�,年底又發(fā)生了蘇舜欽“秋賽”事件�����。按常例�����,京師官署每年春秋都舉行賽神會���,也就是一個同僚聚餐聯(lián)歡會�,詩酒唱和��,歡娛同樂�����。這年的秋賽宴會輪到監(jiān)進奏院蘇舜欽做東,進奏院是皇帝的機要文書處��,廢紙廢品多��,他把它們變賣以后����,個人又湊了一點錢�,便發(fā)起了這個賽神會���,邀請王洙�����、刁約��、王益柔����、江休復(fù)�、梅堯臣���、宋敏求等十來人參加�,偏巧他們都是范仲淹引薦的一時才俊�,是屬于改革派的����。那時的文人官吏��,詩酒不分,還清高狂妄����,政治智慧有時很低級。就在他們推杯把盞�����、酒酣耳熱之際����,王益柔即席賦了一首《傲歌》,其中吟到“三江斟來成小甌��,四海無過一滿壺”�����,牛皮也吹得太大了。這倒無關(guān)緊要�����,關(guān)鍵是最后兩句“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qū)為奴”��,這狂妄到了沒有底線���。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這事��,高興的不得了�����,感覺對改革派最后一擊的機會來了�����。王拱辰何許人也����,歐陽修的連襟��,心中忌恨老歐在文章���、官職上面都壓著他,暗積私怨�,凡是你歐陽修支持的他就反對,沒什么理由�。當(dāng)年彈劾滕子京就是他干的����,就因為歐陽修支持范仲淹?��,F(xiàn)在又是天賜良機���。好呀,你們這幫腐儒��,公款吃吃喝喝也就算了���,還不懂政治規(guī)矩�����,不講政治紀律���,自己撒酒瘋還要皇帝來扶你,你算老幾�����,有沒有君臣之禮�����,周公����、孔子那是什么人呀�,是比皇帝還要高出許多的第一圣人��,他們來當(dāng)你的奴仆����,這還了得����!扣你們一個現(xiàn)行反革命的帽子是一點也不冤的����。于是����,王拱辰果斷出手����,串通監(jiān)察御史劉元瑜等極力彈劾蘇舜欽和王益柔��,狀告蘇、王他們誹謗至圣���,犯有大不敬之罪����,必須處以極刑���。王拱辰等如此死磕,仁宗也不敢馬虎�,派宦官逮捕了全部與會者,令開封府嚴加審訊�����。幸虧韓琦從中巧妙周旋����,案子才從輕了結(jié)���,蘇舜欽永不敘用�����,其他人受降官處分�。不過�,經(jīng)此一案��,改革力量基本上消失殆盡�,王拱辰曾自鳴得意地說,是他把改革勢力一網(wǎng)打盡的�����。十一月�,仁宗頒詔強調(diào)“至治之世�����,不為朋黨”�,不點名地批評有人“陰招賄賂�����,陽托薦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政治意味�����,范仲淹連忙上表自請免職�,次年正月,也就是一過完年�,仁宗就準奏���,免去了他的參知政事,出知邠州�。改革派的另一主將富弼也同時罷政,出知鄆州����。蘇舜欽的老丈人宰相杜衍被指責(zé)“頗彰朋比之風(fēng)”�����,是新政朋黨的總后臺�,隨后沒多久也被罷相���。韓琦上書仁宗為富弼求情,結(jié)果三個月后也被罷職�����。至此����,改革派被悉數(shù)趕出了朝廷�����。在此前后���,新政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幾乎全部廢罷�����。